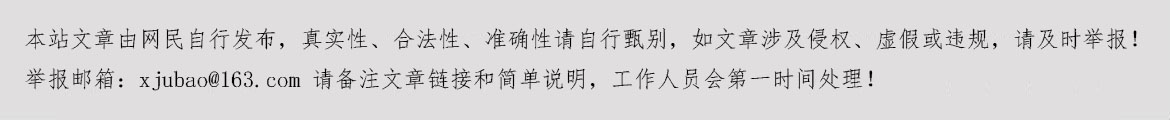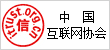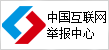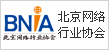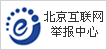“改革市长”张思平和深圳国企的涅槃崛起
2023-05-10 15:57:14
尊重市场一般规律,政府甘于有所不为、“无为而治”是深圳国企异军突起的秘诀。
最近半年研究地方国资发展和国企改革,搜集了大量数据,有很多感悟和收获。就普遍来讲,多数地方的国企改革做的并不是太好,很多省份这二十多年的国资增长速度,甚至比不上通货膨胀速度,国企在无偿占有大量国有矿产、土地和金融资源的基础上,仍在总体经济大盘中呈现萎缩状态。
不过,深圳的国企是一枝独秀。深圳不像北方一些省份那样家底雄厚,至少有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几百家大型国企,而深圳的国资是从零起步;它也不像中西部省份国企那样享有垄断性矿产资源,可以“躺赢”。但是到去年深圳国资总额已经超过5万亿,相当于整个东北三省的国资总量70%。并且深圳市国资效益全国之冠,相当于全国平均国资收益率的3倍以上,2021年深圳国企净利润相当于黑吉辽蒙晋豫等十三个省总和。深圳市国资委主管的企业,有1家进入世界500强,5家进入中国500强;而整个东北三省的地方国企,仅有1家进入中国500强。
所以,深圳不仅有华为、腾讯等中国最成功的民企,也有深创投、深铁置业等改革开放以来成长最快、效益最好的国企,就整个亚洲来讲,可以说是淡马锡外最成功的国企。深圳国企做的成功,是深圳几代改革者努力推动的结果,被誉为“改革市长”、21世纪初主持了深圳历史是力度最大的国企国资改革的张思平先生,是其中关键人物之一。
(张思平,2003年-2010年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分管国资国企、交通、工业等;2010年至2014年担任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并分管改革工作)
张思平先生早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今天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工业经济研究所首批研究生之一,师从马洪、蒋一苇等经济学大家。毕业后分配到湖北省社科院工作,因为表现优秀,工作5年后就被破格提拔为副院长,成为该省最年轻副厅级干部之一。
张思平在80年代,还是积极参与各种经济讨论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同时,作为湖北社科院副院长分管《青年论坛》杂志,这个杂志在80年代是南方重要思想启蒙阵地之一,更因1984年发表胡德平先生的《为自由鸣炮》而引起海内外的关注。《青年论坛》聚集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编辑队伍也是人才济济,其中包括后来创办泰康人寿的陈东升先生。
1988年海南建省,张思平先生被推荐给首任海南省长梁湘,受命组建省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不久,张思平先生发表了《对海南特区建设中若干重大问题的看法》,提出海南不仅仅要做经济特区,还要做制度改革的特区,还提出把海南建设成“小政府”的“国际经济自由区”、“关税特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了多个支持海南振兴的规划纲要,提出海南要在诸多制度改革上先行先试,最近海南要全岛海关封关,建成国际自由贸易区,所有一切均与30多年前张思平先生的设想不谋而合。
1990年海南改革事业出现停顿,张思平先生再蒙马洪先生推荐,并得到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眷顾,来到深圳担任市委政研室副主任,不久,又升任市体改办主任。张思平在深圳这个改革沃土可谓如鱼得水,他主持了深圳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试点改革,大力推动金地集团、华强集团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并且主推行政审批改革,经过改革,审核事项减少近一半,让深圳成为简政放权改革的一个标杆城市。
1997年—2003年,张思平先生赴广州担任广东省体改委主任、省政府第一副秘书长。2003年又回深圳,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分管国企国资改革。现在大家都以为世纪之交国企大改革的时候,像深圳这种地方没有什么国企负担,这是错觉。其实那时候,深圳的国企问题并不比内地轻多少,张思平接手的也是一个烫手山芋。
在90年代,随着深圳特区政府机构逐渐健全、财政逐渐充实,国有企业严重膨胀起来,到2002年仅市属一二级企业就达2000多家,其中85%属于一般竞争性领域,工业、商贸、旅游、地产等各个领域均有涉及。国企的膨胀带来的后果就是效益严重下滑,该年国企亏损面达42%,负债率达60%,邓小平南巡中视察过的深圳明星企业先科集团,短短十年后竟然资不抵债;深圳最大国企深圳石化,负债率也高达370%。
但是深圳国企改革特殊之处在于有充分壮士断腕的决心,果断退出一般竞争性企业,大胆做到有所不为。经过2003年至2005年三年清退,深圳53家一级国企中的36家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国企员工数量也从15万减少到8万。此外,在2006年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又彻底剥离了党政机关所办的300多家企业、2.5万职工。可以说,在全国国企改革中深圳是最彻底的。规模如此大的改革,用张思平的话来说,几乎把深圳市各部门、各国企全都得罪光了,但是当时深圳市主要领导和负责这项改革的张思平还是坚持执行下来,在改革的问题上不给打折扣空间。
经过调整,深圳国企目前80%以上集中于公用事业,而不是那些直接与民争利行业。深圳的国企和民企之间职能做到合理分工,比如在深圳最有代表性的行业——科技创新类产业,国企主要从事为民企发展做基础服务的行业,比如建设科技创新园区、组建产业投资平台、组织协调基础研究等。相比较而言,北方国企则很多还是直接当运动员进入科技产业。
(经过改制,深圳国资从绝大多数一般竞争领域推出,目前市国资委直属企业仅剩下28家)
在对国企的管理体制上,则是坚决破除行政化思维,充分尊重企业自主权,按照市场要求确立公司治理机制。早在1993年,深圳就全面取消国企领导的行政级别;在2003年的国企改革中,深圳市政府授予深圳机场集团等5家大型国企国有资产经营权,独立行使重大决策权、人事管理权、资产收益权和资产处置权,重大决策只需报国资办备案即可。对于企业主要领导人员,国资委改变单纯行政任命办法,改由国资委领导、社会各行业专家组成的提名和评价委员会进行考核任命,副总及以下人员,则可以由董事会决定。
深圳市政府还在授权经营公司中引入了独立董事制度,规定独资企业的外部董事占比必须二分之一以上,控股企业必须三份之一以上,国资委每年建立金融、财务、法律等专家库,为国企聘用外部董事提供参考。这样做充分避免了外行管理内行,与内地相比,深圳国企管理层明显少了官气,而更具有现代企业家气质。
所以,要说深圳国企崛起的秘诀,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无非就是张思平等这一代深圳市领导,老老实实遵循了一般市场规律,在尊重市场经济常识方便做的比其他地方好罢了;无非就是认真做到了国资退出一般竞争性市场,政府退出一般性管理。深圳的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体制,其好处是,市场的市场环境被理顺,民企大发展,也为国企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国企不会因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走向衰落萎缩,反而以与民营经济互利互赢的模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1979年至2022年,深圳国有经济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实现了总资产增长2.6万倍,全市没有一家僵尸企业。
(改制后,深圳国企在与民企和谐共舞中迅速成长,其中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因业绩突出被称为“中国版淡马锡”)
反倒是那些对国有制的认识依然不解放,政府在所有制和国企管理上不愿放手的地方,至今仍持续着国企和民企的双输。因此,张思平先生在他的新书《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中,一再以“过来人”的经验教训提醒大家,政府一定要少管,不要随便给国企提经营目标,也不要不直接投资社会热点项目,这样做只会揠苗助长,既扭曲市场机制,也扭曲企业自身发展机制。
深圳如此改革,也没有让国企蜕化变色,反倒是增强了国企践行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底气和实力。2020年深圳市属国企为国家上缴税金达993亿,大概是吉林省属国企的15倍,或者是八个省税金的总和;在疫情期间,深圳市属国企为租户减免租金27亿(同比山西省属国企减免7000万,吉林减免2100万),筹集了530多亿为民企企业纾困的资金。这充分说明深圳国企效率不仅是走在全国最前列,履行公共责任能力也走在全国最前列。这也告诉我们,只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需求,做好市场化改革,才是国企是体现全民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固守计划时代的意识形态,无一例外会导致国企背离全民性,不利于共同富裕。
除了推动国企改革之外,张思平先生在担任副市长期间,同时还推行了其他多项改革,大大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增加了政府公开透明度。张思平还多次为分管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公开向市民道歉,被媒体称为“道歉市长”。
张思平先生不仅关注某一领域的具体改革,还坚持全面改革的思想。2010担任市委常委后,经过他的努力,深圳市率先恢复改革办,并且作为市委分管改革的领导,他主持起草了2011年至2014年深圳综合改革计划,在公共财政、立法、司法、社保、社会组织、事业单位等领域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改革方案。纵观张思平在深圳和广东工作的20多年,几乎所有工作都跟改革相关,他亲身经历和参与了深圳的改革、发展、壮大关键过程,因此又被大家称为“改革市长”。
可以说,到21世纪后,80年代那种改革理想、改革初心逐渐退潮,然而,张思平是极少数身处政府重要领导岗位,始终保持这份初心和热情的人之一。他因为深圳的这片改革热土,理想抱负得到施展;深圳也因张思平这种有改革闯劲、又有很强执行落实能力,不空谈、不务虚的好领导,而显得与众不同。
前几年张思平先生退休后,保持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本色,创办了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改革发展的重要议题,还组织过好几届“大梅沙论坛”,成为南国重要政经高峰论坛。此外,他利用退休闲暇时间,奋笔著书,先后完成了多本著作,其中《深圳奇迹》(中信出版集团,2019)可以认为是对深圳城市发展史、改革史记录最详细的一本著作。
最近出版的《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四十年》(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3)是他的另一部力作,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在发展中,都遭遇了制度瓶颈,出现了效率、效益危机,唯独深圳的等少数地方国企突破了这个天花板。张思平先生从历史亲历者和创造者的角度,记录了深圳国企改革历程,并提出了自己的系统思考和反思。这本书最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完全站在一个客观角度,丝毫没有为自己当年的成就自吹自擂,而是反思了当年很多改革不到位的地方,以及对当下国企改革提出了很多逆耳忠言。此所谓种种,都体现了他作为纯粹改革人求真唯实的本色。(本文原文发表于财新网)